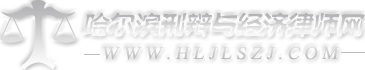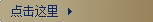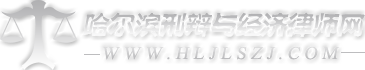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原权(知情权)的请求权,一种是为保护原权而产生的次生请求权——侵权请求权,对后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属于专家侵权责任。本文对消费维权中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的地位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
(一) 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在民法请求权体系中的地位
在早期罗马法上,由于私权体系并不发达,权利人不得不以诉讼的方式实现其权利。 这也使得权利的行使是通过诉讼来发现,而先有诉讼后有权利。自从德国民法创造出请求权概念之后,这种限制私力救济的体系才得以瓦解,私权与司法保护之间的媒介才正式由罗马法时代的诉讼转变成请求权。请求权的提出使得所有民事权利的私权救济手段都可以通过一个统一的概念来认识,从而使得民事权利制度构建更加体系化。 在以请求权构造的私权保护体系中,任何权利,无论是相对权或绝对权,为发挥其功能,或回复不受侵害的圆满状态,均须借助于请求权的行使。 请求权也因此被分为基于原权利的请求权和保护原权利的请求权,具体而言,这种请求权体系化的划分是根据绝对权和相对权划分而定的。这种以请求权为链接点将民法中绝对权与相对权体系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绝对权相对化的过程。私权受到侵害时,有两种请求权产生,一种是基于原权利本身的请求权,另外一种是基于侵害原权利而产生的次生请求权,原权请求权的产生是以存在的绝对权或相对权为基础的,其存在目的是为实现和保护绝对权或相对权的圆满状态。而次生请求权与原权请求权的性质不同,它是基于他人违反民事义务或侵害民事权利而产生的权利,其实质是权利人请求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次生请求权主要表现为侵权请求权,是基于权利被侵害而生的权利保护的请求权,因而其基本性质虽然也是请求权,但它是次生的请求权。 这两种请求权是相互联系互有分工的:原权请求权着眼于回复权力行使障碍,而次生请求权是侵权法范畴,是对已经侵害的权利给予赔偿。由此可见,单纯依靠任何一种请求权去保护权利,是远远不够的。原权请求权是“未雨绸缪”,次生请求权是“亡羊补牢”。
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从近代以来已经成为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从性质上看属于绝对权,这种绝对权的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任何有侵权之虞的人,不特定的义务主体在没有确定之前不能产生相对关系。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来是隐藏在绝对权力之下的,只有到侵害发生之时,请求权才得以彰显,进而将绝对权利相对化,正如梅仲协先生所言,请求权系权利之表现,而非与权利同其内容也,就绝对权而言,在权利不受侵害时,其请求权则隐而不现,然若一旦遭受侵害,则随时可以发动。因此基于消费者知情权而产生的请求权,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技术上手段上的权利,它的功能是维护知情权不受不法侵害。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行使的前提是知情权有受到侵害之虞,或者已经受到侵害,其行使的手段也应该有基于知情权的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两种。具体来说,当知情权受到妨碍、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之时,权利人有权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此时权利人可以行使原权请求权维权;但是当损害已经发生,回复原状已不可能或无必要之时权利人就只能选择行使次生请求权,即提起损害赔偿的侵权之诉了。
(二) 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的特殊性
消费者知情权不同于其他绝对权,它虽然是消费者基本权利之一,具有独立性,但是从功能上说,实际上是一种辅助性的权利,这种知情权虽说具有绝对权的性质但是却不能摆脱和其它权利行使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害,消费者被错误导向购买商品而致损,这时按照侵权法中因果关系界定,致损原因其实是产品责任,而不是因知情权受侵害产生的误导行为;反过来看,知情权受损产生的误导其实并不完全是消费者致损的直接原因。因此在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的把握上要特殊看待:应以原权利请求权为主,次生请求权为辅,着重维护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这是因为:第一,次生请求权是第二位的补偿性权利,在行使过程中一般要求侵害人存在过错,权利人负有举证责任,而且在法院权衡过错时会综合量化分析侵权人过错行为对权利人的影响。对于消费者知情权这样的辅助性权力是很难量化的,举证责任更是难之又难。尤其是在消费者知情权发展急剧扩张的现阶段,义务主体纷繁复杂,网络自由与言论自由常常会对知情权的过错方产生抗辩,侵害知情权导致行为致损的因果关系更是一个复杂谜团,因此主张消费者知情权侵权请求权是不现实的;第二,消费者知情权请求权的请求权基础在我国目前法律规范框架下,主要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和《产品质量法》第24条规定,这两个法律规范从本质上是分别从原权请求权和政府监督责任角度来规范的,尤其是前者,更加类似于权利宣誓般的规定。这两个规范更侧重于对消费者知情权的维护,至于被侵害之后的损害赔偿,大都倾向于产品责任请求权角度提起;第三,我国目前没有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这无疑使单纯提出消费者知情权侵权请求权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综上所述,在我国现阶段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虽然有原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两种方式,但是侧重原权请求权似乎更为妥善。